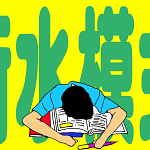Welcome to RealTime Mandarin—a resource to help you bridge the gap to real-world fluency, stay informed about China, and communicate with confidence—all through weekly immersion in real news.
This exclusive content is part of RTM Plus, our premium membership.
👉 Upgrade now to unlock full access and improve your Mandarin every day!
中美间的第二次关税战开始了,其强度远超2018年那一场。彼时,美国为中国2000亿美金的商品加征了25%的关税,中国为60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加征了10%或25%的关税。而这一次,双方对彼此几乎所有出口商品都加征了超过100%的关税,已足以让绝大部分贸易停摆。
这是一次力度空前的经济对抗。舆论场上,这场关税战却显得意外地“安静”——甚至有点分裂。有人说它没那么严重,对美出口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4.7%,完全可以靠内需和其他市场替代;也有人将它视作战争的前奏,认为整个国家需要进入“战时体制”。
更令人困惑的是,这场关税战一方面动摇着现实世界的经济基础,另一方面却又像网络迷因一般,在短视频、段子和表情包中变得轻盈乃至荒诞。特朗普自带的争议性与娱乐性,进一步稀释了危机感。于是,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剧变,被裹挟进了一种“严重,但又感觉不到严重”的氛围中。
所以,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风暴?它的严重性为何如此难以感知?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场关税战的真实气候?
企业出海的两难困境
有一种很流行但轻率的说法认为,关税战带来的影响不大,只需通过“转口贸易”绕道东南亚,中国商品照样可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,因此对中国冲击有限。
这种理解并不准确。关税的课征对象是商品的“原产国”,也就是说,几乎所有已完成包装的商品,都无法通过简单的转口规避美国关税。有人可能设想,将产品的最后包装环节放在其他国家即可,但这也行不通。国际上对“原产国”的认定,遵循的是“实质性转变”原则——产品必须在加工国发生根本性变化,才能获得新的原产地资格。190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,只有当最终产品在名称、特征、用途上都发生显著变化,才算重新定义原产地。
“原产地欺诈”是美国海关严格查验的行为。例如CEK集团曾将中国制造的钢丝衣架转运至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,再出口至美国,并虚报产地以规避187%的反倾销税,最终被罚1200万美元(相当于3倍关税)。钢丝衣架尚且如此,复杂产品的转口成本只会更高。
当然,原产地认定不是百分之百准确,但从早年的糖精、丝带,到近年的衣架,这类操作早已有案可查,不是什么应对“2025关税战”的新发明。指望靠转口贸易大规模破解关税难题,并不现实。
更直接的出路是将产能整体迁往低关税国家,实现“出海”。这也是上一轮关税战后许多企业的应对策略。但这个办法本身也有矛盾。就在4月8日,有消息称在线快时尚零售商希音(Shein)计划将部分供应链迁出中国,结果在商务部与其就“供应链多元化”沟通后取消计划。
这固然缓解了个别企业的压力,但如果像希音这样的公司最终将产业链转出国内,意味着就业、税收、创新等都随之流出。如果是一家在A股上市的公司,或许对国内仍有资本回报;但若是一家完全搬至东南亚的民营企业,那它就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了。
因此,无论是转口贸易还是产能外迁,都是代价高昂、效果有限的权宜之计。面对结构性的关税压力,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更加系统性的应对方案。
从订单到就业:集约化体系的脆弱一面
中国对美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14%,就算这些出口完全丧失,会不会影响也相对有限?其实,这14%所引发的“涟漪”,远比想象中更深远。
首先,从行业来看,对美出口的重点领域包括消费电子、家电、纺织玩具等。其中消费电子和家电在国内早已遭遇产能过剩。更进一步,上游支撑这些产业的中低端芯片,也处于同样的困境。以消费电子为例,中国对美出口占整体消费电子出口的22%左右。如果这22%的订单突然消失,将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冲击,并波及芯片制造等上游产业。
我们常说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“工业体系完备、产业链齐全”。但在关税战背景下,这种优势也转化为脆弱性:一个终端产品受挫,可能带崩整个产业链。虽然很多出口企业集中在沿海,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却往往来自中西部人口大省,例如河南、四川。当沿海组装厂削减产量,内陆供应商也必然收缩,经济压力由点及面传导开来。
以电子产品为例,广东负责组装,但四川却是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全国第一。此外,四川在集成电路、碳化硅、稀土等领域也居全国前列,这些都与电子出口息息相关。可见,关税冲击不会止步于出口企业,而会沿着产业链深度扩散。
其次,产业高度集中也使局部问题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。仍以广东为例,格力、美的、海信、TCL等家电巨头几乎都在广东设厂,周边形成完备上下游体系。一旦订单减少,首当其冲的是裁员、休假,继而影响地区的消费、住房、服务等多个层面。今年国家高度重视提振消费,而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滑坡,无疑会对国内消费信心和能力形成打击。
换句话说,关税的直接目标是出口,但它的间接后果是对整个社会就业、收入、消费的全面波及,最终变成一个整体经济问题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层面的“次级传导”。虽然对美出口占比不到15%,但沿海出口省份如广东,正是承担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财政来源。以广东为例,2024年其工业总产值超20万亿元,出口约5.89万亿,对美出口1万亿,占比17.4%。考虑到广东工业税收占比约40%,对美出口的滑坡直接拉低税收近2%,对地方财政打击不小。而地方财政下滑,意味着中央必须增加转移支付负担,进一步挤压全国性支出空间。
当然,也有一些临时性的利好在发生。就在本文写作期间,特朗普宣布将对电脑、手机等总额约3900亿美元的商品给予关税豁免。其中约1100亿来自中国,约占中国对美出口的20%。这对广东及相关电子产业链是一个重大缓冲。
但这也只是暂时的。20%被豁免了,那剩下的80%怎么办?
从《Project 25》看两次关税战的不同
既然这场关税战对中国影响如此深远,其余的80%部分还有希望止损吗?是否应争取尽快结束?